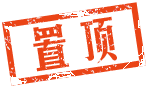引子:珠玛的歌碟
一阵沉闷的脆响,我接到了大学入学通知书……
一阵沉闷的脆响,加央卓玛从四楼教室的顶层飞跃下去……
加央珠玛,一个瘦瘦小小风一吹都像草叶似的左右摇晃的女孩子,一个咬着嘴唇对谁都是一副羞涩笑容的女孩子,也会做出这样的惊天动地的事?她与我不同班,却住在我的楼上,我们天天见面却没说过一句话。活跃的来芹爱说她的事,说错拉来的珠玛脑子真笨,考大学肯定没戏。不过,她嗓子好极了,会一支接一支地唱仓央嘉措情歌,会把一支音调很高的歌唱到天上,再回到地上旋五百二十圈也不打一个结。她的梦想是做歌星。我天天都能听见有很高的音符从那黑黑的窗洞里飞出来,把弯月唱得更加明洁,把早晨的太阳唱成一片金色。可从没想到,她会同她的歌声一起飞出窗外。
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原因跳了楼。她的父母悄悄地火化了她,捧着她的让一块白布包着的骨灰悄悄地走了。
就在那个晚上,那孔窗洞里又传来了嗓音很高的歌声,我越听越觉是珠玛的声音,只有她的嗓音才能在高到极处时,还能打好几个旋又向上绕去。
在那东边的山顶,
升起皎洁的月亮,
美丽姑娘的脸庞,
浮现我的心上……
我踩着歌的节拍上了楼,心里怯怯的。
我是亲眼见到珠玛的骨灰让她的母亲伤伤心心地捧走的,也不相信这世上真有鬼魂什么的。可我心里还是怯怯的,颤着手轻轻地推开了虚掩的门。
昏黄的灯光下,来芹孤独地坐在堆了一地废报纸旧杂志的地板上,一个老式音箱哧哧扎扎地响着,珠玛在破损的磁带里唱着她平时爱唱的歌。来芹抬头望着我,圆胖的脸上满是泪水。
在珠玛的歌声里,我与来芹什么话也没说,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的头发和湿润的脸磨擦着我的脸和脖子,身子还在伤心地抖。我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喉咙里好像哽着一口痰,咳嗽了好几声都咳不出来。我嗅到了股刺鼻的气味,转过头朝四周看看,说:“你点了酥油灯?”
她说:“酥油灯灵,可以把珠玛的魂招到屋里来,”
我的心里便莫名奇妙的一阵颤动,推开了紧紧贴在我身上的她。我笑自己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听着那首伤心的歌曲就跑上了楼。我算是什么?还拥着胖胖的来芹同她一起为一个只见过几面,却只说过一次话的女孩子悲伤地哭泣。我同珠玛说的那次话还是吵架,吵得我赌气一下午没吃饭,喝了一肚皮的啤酒。
事情很简单,高考的前一天,她抱了一大堆影碟从我门前过,我刚好开门出来,她尖叫了一声,哗地一声影碟从她怀抱中飞了起来,花瓣似的掉了一地。她赌气地望着我,脸颊红红的,一声不吭地把嘴唇咬出了乌黑的牙印。本来,我也一声不吭地把地上的碟片一张一张地拾起来,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我却锁上了门,夹着几本书看也不看她,就朝外走。
她的眼睛红了,有眼泪掉了下来,对着我的背影一声吆喝:“站住!”
我回头朝向她,脸上冷冰冰的,把手抱在胸前。
她指着地上说:“你做的事,你就不管了吗?”
我冷笑了一声,说:“碟片是从你手中飞出来的,管我什么事?”
她的脸更红了,说:“你不开门,我的碟片会飞吗?”
我哈地一笑,走了过去,指着碟片问:“喂,是我吓着了你们吧?我样子那么吓人吗?吓着了,我给你们道歉,你们爬起来吧,别躺在地上装死狗。”
她瞧着我,脸色变白又变红,大喝一声:“你疯了。发什么神经!给我捡起来!”
我想了想,说:“我给你捡可以,你得给我一张歌碟作为报酬。”她冷笑着看我拾碟片,拾完后便抢了过去,头也不回地往楼上走去。
我急了,说:“给我的碟片呢!我不会给你白捡的!”
她没理睬我,掏出钥匙开了门,又把门摔得很响。
就那么一回,她扔给我的还是冷冰冰的脸色。今天,我却在为她点的酥油灯前流了一把伤心的泪。天呀,这是怎么回事?我看看这间屋子,同我的那间差不多大,只是多了女人的梳妆台,一台已快进古董店的老式音箱,一个能烧牛粪的火炉。两张床铺上有女人的细软洁净的被子,窗前晾晒着女人的秘密。屋内有股男人嗅了心里就发慌的气味,我有些坐不住了。
来芹却拉着我,不让我走,说:“你不能走。我知道你考上了,珠玛也知道你考上了。我和珠玛都没考上,我还想复读。你不能走,珠玛也在说你不能走。陪我喝点酒,算是为了珠玛,也为了我向你祝贺。”
我头有些晕了。我为了什么珠玛?为了同她的那次不愉快的吵架?还是为了她制造的那一声闷响,给我送来的录取通知?来芹却把酒倒好了,把两袋焦盐花生米哗地倒在桌子上,又在火炉上烤了两条干牛肉。她说,牛肉是珠玛从错拉小店里买来的。
她望着我,眼睛眯上了又大大的睁开,好像是专门向我透露她内心的欲望。我的心在狂跳,脸却转向了让黑夜淹没的窗外。她喝了一口碗里的酒,望着亮晃晃的酒碗说:“你心里有疑问吧?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好多事想问,是不是?”
我哼了一声,没理她。
她说:“珠玛早就想跳楼了。好几次都是我把她拉住了,你别担心,这与你无关。那是珠玛自己的事,她不让我管,也不会让你管。”
我坐了下来,她把酒碗推给我,让我喝下去。火炉的火小些了,喝点酒才能暖身子。我没喝,她却讲了,说:“真的与你无关。珠玛是痛恨那个叫索南平措的小男人。索南平措你听说过没有?我们学校那个会画画的才子,前几天就拿了读美院的通知。他不像个男子,没有男人的责任。他让珠玛怀上了,就要跑了,好像那一切事都与他无关。那天早上,他来了,扔给了珠玛两百块钱,就要走了。他对珠玛说,他从来就不认识她。下一世也不会认识她。珠玛就哭了,那可怜无助的样子让人担心死了。不过,在太阳出来时,她就笑了,很开心的笑了,还唱了歌。我还敲着茶碗给她打拍子呢!后来,她就从窗子上翻了出去。哦,不说了,我都伤心死了!”
我嚼了口干肉,硬硬的有些干涩。我觉得是在嚼珠玛的肉,就不想再嚼了。啤酒我却喝了不少。来芹也喝了不少,喝得脸颊艳艳的像帖了两片花瓣。我的头晕晕的,像顶了个沉重的东西,怎么摇晃都扔不掉。我站起来,冲她晃晃手,说:“我得走了,再不走我可能会倒在这里爬不起来了。”
她却惊慌地一把抓紧了我的手臂,说:“你不能走。你走了,珠玛要我讲给你听的话,我讲给谁去呢?”她的手绕过来,又把我紧紧地箍住了。
她让我坐下,在我耳边说:“珠玛说,她欠你一张碟片?是吗?”
我笑了一声,说:“她谁也不欠。”
她说:“珠玛说,她欠了。她就刻了一张她自己唱的仓央嘉措情歌。她说你喜欢仓央嘉措情歌,她听你唱过。她要我无论如何都要送到你手里,歌放完后,你就拿走吧。珠玛说,这幢楼的男孩子她就喜欢你一个。”
我朝那盏酥油灯望去,灯苗跳溅了几下,火旺了,火苗子一蹦老高。珠玛是躲在火苗子背后吧,她也听了这话,是在向我说些什么吧。我的鼻腔有些酸了,忍不住时眼前就有些昏暗了。
我说:“放开我,我得走了。我老爸今天要来。”
她没放开我,站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看到了她眼眶内有两颗火苗子燃得很旺,带着酒气的血慢慢地涌上了脖子。她说,珠玛是错拉那地方的人,那里的女人都会唱好多好多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歌。珠玛说,她们都是仁真旺姆的后代,就是六世达赖佛的初恋情人,那个仙女一样温柔漂亮的小店主女儿的后人,六世达赖佛那时叫阿旺嘉措,还没坐床布达拉宫呢!
我想起珠玛的那双眼睛,深遂多情的眼睛,还有眼眶内打转的泪水。我信了,那双眼睛就是情感的种子,播在什么地方都会生长出开满火热鲜花的树。
来芹看着我,眼睛闭上对我说,她想和我接吻。
我有些惊慌,也有些胆怯,想不出该怎么办。她的嘴唇却把我的嘴巴紧紧地叼住了,那一刻,我便淹没在一滩温暖的带着酒香的水里了。
那是我第一次同女人接吻,我记忆里便刻下了惊慌、胆怯和温水。
我离开了她的还放着珠玛歌曲的屋子,逃跑似的下了楼,把这幢潮湿的红砖楼扔在背后,走进艳艳的阳光里才舒心地喘了口气。几天后,我就会把这幢楼彻底地扔到记忆中去,再也不回首……
情人毫无真情,
如同泥塑菩萨,
好比骑上了一匹,
不会奔跑的劣马。
尊敬的六世达赖佛仓央嘉措有首歌就是这么唱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