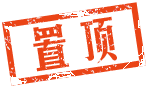|
开头还是结局
丁铃,丁铃铃…… 橐橐,橐橐橐…… 半夜里,骤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或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孤身一人缩在宽阔暗黑的老屋子里的你,会感到惊悚与恐惧吗? 我不怕电话铃声。尽管两年前,丈夫就带着八岁的儿子去了美国,这空荡荡的屋子就只剩我一人了。我习惯了寂静的夜晚湿润的江风在窗玻璃上磨擦出的哗啦啦声,听惯了老鼠和不知名的虫子在床角或衣橱背后弄出的嚓嚓声。我的职业,也使我常常在夜间对着电话筒,与一些不愿说出自己姓名的男人或女人聊天。我和他们一起在深海般暗黑无底的夜里下沉,下沉,在夜的最深处停下来,用温软暖和的话语为他们揩去沾满脸颊和心灵上的伤心眼泪。 这是我的职业。我叫聊聊,当然不是我的真实名字。我在《浪州晚报》生活副刊主持一个叫着情感夜话的专栏,报纸上印着两个大字:倾诉。那些在情感旅程中经历了风雨波涛的男男女女,都把憋了满肚皮的酸涩苦痛的东西,找我倾吐。我也乐意倾听,同他们一起欷嘘流泪。或用一些老生常谈,来缓解他们堵塞在心里的淤泥。把他们的故事编织出来,多用些煽情的词语,再赚取读者们的眼泪。 我就是这样一个情感垃圾筒。 我不怕电话铃声,却怕敲门,特别是在这个阴雨绵绵的深夜里。 我刚与一个悲伤得想自杀的失恋者聊了许久,心里还堵着他留下的阴冷,那敲门声就响起来了。 橐,橐橐橐…… 敲得很轻很柔,像音乐会里的鼓点似的响着。我不吭声,裹在棉被里,望着在响声中颤动的门。那声音就这样响着,我的心也跟着门板一起颤抖了。我的手伸出来,摸着了床头柜上的电话,拿着话筒又不知该给谁通话。 我拨了楼下传达室的电话,守门的老头很负责,他肯定会上来看是谁在敲门的。电话铃一遍遍响,却没人接。我想,传达室老头不会不在,也不会睡那么死。可比敲门声更急的电话铃声,怎么会吵不醒他? 橐,橐橐橐…… 敲门声仍然不倔不挠。我想起了一个人,就住我隔壁。那个叫候一桃的小伙子,一个来报社快两年的大学生。他现在是报社最有朝气的记者,有张什么时候都充满阳光的男孩儿的脸,还有那双底很厚很重的登山皮鞋,踩踏得楼板吱嘎吱嘎响。他奔忙在白天,我忙碌在夜晚,所以我们平时不常见面。有时在楼道中碰见了,也笑着脸,侧侧身子让让路,没有在一起说过话。我在号码簿里翻了个遍,也没找见他的号码。我想起报纸上该有他的电话,就在报纸上寻找着。 有他的电话,不知是办公室里的还是他的卧室的。拨通了,却没人接。 敲门声却更响了,门板摇晃着,我真怕已经开始朽脆了的门板让他敲得塌了下来。 “谁呀?”我大着胆问了一声。 敲门声停了一会儿,没有人回答。只一会儿,又不倔不挠地响起来了。 我在四处找着能够自卫的东西。除了柔软的枕头,只剩搬不动的沙发,我什么自卫的东西都没有。惨呀,我心里说。如是打劫的,我只有束手就擒,让他撬门进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我抓起桌子底下一个硬硬的东西,看了一下也有些发笑,那是我儿子以前最爱玩的变形金刚塑料玩具,那怪模怪样的机器人手里抓着一把塑料弯刀。不过,拿在我的手里,还是为我壮了胆。我悄悄地走到门边,轻轻地拔开猫眼,对着小小孔洞看去。暗淡的灯光下,门前的那人缩小得像个豆点。 我看了许久才看清,那人就是住在我隔壁的记者候一桃。 我故意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说:“什么事呀?我都睡了。呵呵,好困!” 门外的人说:“聊聊,是我。住你隔壁的候一桃。对不起,这半夜里,我想打挠你一会儿。” “什么事?天亮了说行不行?” “天亮了,就什么都说不成了。明天一早我就走了,离开这里了,不会再回来了。我不想装着一肚子不舒服的东西走,想找你聊聊。” 我迟疑了一会儿。我这个垃圾筒,让本社的人来倾吐,这还是第一次。我拉亮了门道前的灯,开了门,那个叫候一桃的小伙子便裸露在雪亮的灯光下了。 “真不好意思,这么深夜了,还来敲你的门。”他脸红了,带着羞涩的笑,眼睛不好意思地眨动着,显得青嫩青嫩的。我仔细看着他的脸,这两年来他还是有些变化。那时,他是一个脸上有着菜青色的大学才子。此时,脸颊上有些肉了,下眼睑也有了浅浅的眼袋了。嘴唇上的短短的胡桩是粗硬的,像脱了毛的刷子。 我把他让进屋内,他却从怀里摸出了一瓶酒,是红葡萄酒,俄罗斯的。他说,是他的一个老朋友留给他的,那位老朋友可能不在人世了,酒却在。此时,喝着它,才有倾吐隐私的胆量。 我给他准备了杯子。他要给我倒,我没让。我不愿在倾听的时候喝任何带酒字的东西。 他笑了一声,把杯子朝灯光举了举,喝了一大口。他的脖子上便涌上了一片红色。 “我要走了,明天?嘿嘿,看时间该是今天了,天一亮,我就剩船离开这里了。”他的话让我有些吃惊,问:“干得好好的,为啥要走?” 他转动着酒杯,看着玻璃上反射的深红色的亮光,脸上笑得很难看。 “我有儿子了。有个女孩怀上了我的儿子,她现在那座叫康定的高原小城里等我。” 他说得很平静,却让我差点跳了起来。瞧不出,这毛头小伙子脸还很嫩,一挤可能会挤出水来。心里却熟得快落地成泥了。我想,这里面肯定有我的栏目感兴趣的故事。我给自己冲了杯滚烫的咖啡,想提提神,和他聊一个通宵。 他看着对面那一壁厚厚的绒布窗帘,说:“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吧,你这里太闷了。” 我拉开窗帘,把窗户虚一条缝隙,很冷的风便灌了进来。还有一声声尖锐的汽笛,把窗玻璃冲撞得哗啦啦响。他轻笑了一声,说:“你和我屋内一样,拉开窗就看见千汇码头。” 我说:“我喜欢闻江风的味道。” “许许多多的日子里,我都看着码头,看着码头下那滚动的一江浑水想,我们人类,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不是都像个码头?我们是不是像那航行的停靠的大大小小的船只?我们停泊,我们行走,我们的情感和欲望,都同这冷冰冰硬梆梆的码头有关。没靠码头的,都在找寻合适的码头。靠久了旧的码头,会寻找新的码头。我们在行走,在寻找,直到破了朽了,丢弃在码头的石滩上。” 我瞧着侃侃而谈的他,瞧着他近视眼镜片后的眼睛鲜亮起来,那张脸混和着男孩的稚气和苍老的疲惫。他盯着杯中的酒,没喝。轻轻地摇晃酒杯,让血红的酒晃荡起来。一抹红色从他青嫩的下颌处升起来。他抬起头,看着另一扇仍然遮着厚实窗帘的窗户,说:“这扇窗怎么不开呢?” 这扇窗我是从来不开的。可此时,他心内淤积很久了的东西需要有扇窗户来输导输导。我拉开了那扇窗帘,也把窗户虚了一条缝隙。那窗户正对着一幢很有古典味的楼,在夜雾里青得发黑。那是报社的老宿舍楼,里面住的人正沉没在深深的梦乡里。他来到窗前,眼光从一楼朝上升着,到了八层的顶楼,又慢慢的滑下来,停在了与我的屋子平行的那扇窗户前。他说:“那扇窗里住着谁,你知道吧?” 我说:“你是说我们新闻部的马大主任?” 他笑了一声,又平静下来,说:“你猜猜,她此时在干什么?” 我看看黑洞洞的窗户,说:“睡觉呀。你以为都像你,一只没有瞌睡的夜猫子。” “哈,”他笑了,笑得很大声,说:“她会睡觉?这个晚上,她就是躺在床上,都睡不着。” 我不明白他为啥这样说,也不想追问别人的隐私。他又回到桌前,把酒杯端起来,对着那扇窗户举了举,好像在为什么事与他的主任干杯。他喝了一口,喝得很狠,杯里的酒只剩一小滴了。他的眼里便有了血红的酒味。 “我的故事,就从那扇窗户和窗户背后的人开始吧。” 他的话刚落,那扇窗户的灯光便亮了。有个人影在窗前闪了闪,又拉上了厚厚的窗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