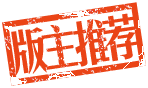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蝶纹沧海 于 2012-3-26 11:51 编辑
枝头只有一只鸦,毛羽蓬松,没有聒噪,像片贪恋枯枝老也飘不走的焦叶,悬在这棵秋后枝秃的老杨树上。寒风夹着雪片在树隙里呜呜吼叫,枝条劈里叭啦互相抽打,搅得枝头老是裹着层灰蒙蒙的雾气。 我立在树脚,周围是一片枯黄的串满冰条子的茅草。我知道,母亲的坟墓就在茅草丛中。茅草密密匝匝,杂毛般蓬乱,淹没了母亲的那座红土包。 十年前,这里还只是青嫩青嫩的草皮子,掀开草皮就是赤红的土,,浓重的碱味就扑面而来。土质松软细腻,不时还刨出几根蚯蚓和土毛虫子,也同这泥土般血红。母亲的棺材是黑色的,搭条雪白耀眼的纱布。母亲的棺材就放进了红土坑内,像血红的眼眶嵌进了黑亮的眸子。母亲就用这种忧伤痛苦的眼眸望着我,树枝上的雪粉融成了冰珠子,叭嗒叭哄滴着,冰凉的沾在脖颈上,像是眼泪。矮胖的风水先生手心摊着罗盘,大声吆喝,肿泡的眼睑冻得青紫。 “往右靠,往右靠,头要直对高山头。妈的,眼珠是不是牛尿泡塞的,偏到耳根下了。” “还是对着下面那条河吧。她活着时就喜欢这条河。”父亲说。 “放你妈的臭屁!这伤人阴德,败坏风水的事老子干不来。看看,多好的风水,左青龙右白虎,上靠天,下掘财,够你家享受几辈子了。“风水先生的唾沫溅了我一脸,有种鸟粪的臭味。 我木呆地望着那只鸦,它像睡着了,头塞在羽翅下,对下面的人和事理也不理。十年后,我又看见那只抓紧树枝熟睡的乌鸦时,真以为它整整睡了十年,从未离开过那根树枝。 砌坟包的人们忙忙碌碌,填土码石,坟包造成了,四四方方,像幢小楼。父亲突然呜呜哭嚎起来,弟弟使劲掀着坟上的石头哭红了眼,两个舅舅也低声啜泣。雪又纷纷扬扬飘洒起来,风嚎得像哭。 我没有流泪,那时,我还小。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爱哭。我望着枝条上的那只鸦,它沉默我也沉默,它不哭我也不哭。 母亲是不讨厌乌鸦的,有时,她听见几声哇哇鸦叫,就欣喜地抬起头,说天气该转暖和了。有时,她又愁苦地说:“听听,乌鸦又叫了,不知什么地方又死人了。”她说后,就很得意地望着别人,好像只有她懂得鸦嘴里的话。我心里蹦出一句话,是母亲教我的。她说只要对着乌鸦说了,再凶的家伙都会缩着脖子仓皇逃走,百验百灵。 “哇哇,把你吊起打,打!” 我大声喊了,声音在周围的墙壁上撞出了一片嗡嗡。那只乌鸦再不敢沉默了,抖动惊异的羽翅,缩缩脖子,像一根压得很扁的弹簧,猛然松开,箭一般笔直地朝空中射去。哇哇,忧伤的歌声冰雹似的朝雪地劈劈叭叭扔着,四周寒冷极了。 十年后,我站在呆立枝头的黑乌鸦下面,再也喊不出那句话了。我稚嫩甜润的嗓音丢失以后,总是带着粗哑和凶狠。我再喊出那句话时,肯定像只疯狼在荒野吼:“我要喝血!” 我有些沮丧了。风抚弄着杂毛似的荒草,我不知道母亲的坟墓淹没到了何处。风撕开的草隙间,我看见许许多多的鸦羽,黑色的白色的全闪着耀眼的光。 我喊不出那句话,是不是我已经长大了呢? 我真正长大的时候,却觉得自己只是个淘气的小孩子。 那年,我十七岁,无所事事,便满山遍野地乱窜,玩玩打猎的游戏。草鹿、岩羊我都打过,一天不砰砰放几枪,就像有屁憋着不放一般的难受。 我扛着枪,踩着软软的草地朝河滩走去。太阳悬在天边,欲升欲坠,红得像血。软绵绵的草地一踩就汪一脚的绿水,咕哧咕哧响着。四周静悄悄的,草缝中连只野兔都看不见。我站在河岸边,脚下的河水忿忿地吼一片白浪。我紧张了,预感到那棵孤立河岸的老杨树背后歇有野物。我咕哧咕哧踩着草皮朝那里走去,靠在树身,屏住呼吸。我敏捷地跃出树背,,平端着枪,指头在扳机上颤。什么也没有,地上晃一片蓝焰焰的树影。我恼恨地靠着树身,好像这么亮的太阳全是虚设。那该死的草獐哪里去了?它常常来河边喝水,然后就躲在树后睡觉。该死的家伙肯定死了,不知尝了谁的子弹。我巡视四周,草滩平坦坦的伸进远处灰蒙蒙的雾气中,银塔似的雪峰傲立在雾气之上,像悬挂在蓝湛湛的天幕上。没有一丝风,我真希望有一只活物,即使是一只麻雀,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端枪、瞄准、射击。那时,空虚的我就有这种焦躁之心。 那两只呆头呆脑的乌鸦落进了我的视线。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几声哇哇响在头顶,我竟然惊骇得缩紧了脖子。它们就站在老杨树上,靠那么近,互相梳理着油黑的毛羽,勾着脖子睡觉。这是对情侣。他妈的,丑模丑样的乌鸦也有情侣。野性的血冲得我满脸滚烫,四肢抖颤。我端起枪瞄准着。一枪穿个连环,噗噗掉下两团肉,砸在草地上的声音肯定很好听。我没扣响扳机,一丝恶毒的笑在我脸上颤着。我改了主意,只打左面翅膀上有团灰色的那只,那肯定是只母家伙。我想看那只公家伙失去伴侣后如何表现。 砰——!枪声震得树枝一片哗啦啦响,那只乌鸦像片枝叶摇摇晃晃朝下掉,周围是一片炸飞的茸毛。另一只惊愣在枝头,过了许久才暴出一串惨裂的叫声,箭一般地朝远处射去。 呜哇,呜哇…… 那悲伤欲绝的声音又从远处响了过来,在我的头顶,在清冷的河滩上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出了它身上的仇恨。它耸起翅膀,脚爪抓成了鹰爪似的尖利。它想向我进攻,几次猛扑下来,我举枪瞄准,它又胆怯地逃开了。不久,它失望了,偏过身子,朝河滩上落去。呜哇呜哇地叫着,像在哭泣。它站在僵死的伴侣身旁,喙头对着喙头,它在呼唤伴侣醒来吧?过了许久,草滩上开始起风了,周围骤然凉了下来,它缩着脖子,展开羽翅,一串绝望的鸣叫,朝上笔直地升去…… 我仰起脖子,看它越来越小,成了一粒黑豆,成了一颗针眼。我感到眼心有些疼痛了,忽然,那黑迅速朝下掉来,越来越大。我惊呆了,那家伙竟然紧抱双翅,头下脚上,狠狠砸了下来。下面是一堆乱石滩,砸在上面的声音使我想起了摔碎的玻璃瓶。它在石滩上弹着,滚到了草地上,脚爪痛苦地抽搐,慢慢地僵硬了。 我的枪掉在了地上,紧搂着粗壮的臂膀,下肢却一阵阵疼痛。我在一片呜咽的寒风中瑟瑟抖颤着,竟没有勇气朝那两只死乌鸦靠拢。 不久,我玩枪走火,枪弹打穿了我的腿骨。我想,这是报应。母亲说过,乌鸦是最有灵性的鸟。母亲喜欢乌鸦并没有错。后来,同伴约我去火地村,同伴说那里可以见到世界上最大的鸦群,还能见到天葬时,乌鸦和秃鹰争食人肉块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我竟然敢到难耐的恐惧,死也不肯去瞧那些漆黑如炭的家伙了。 我离开草原时,珍藏了一幅画,是我用两口大铁锅同一位藏族老艺人换的。画面很简单,就只一个金黄色的太阳,中心站着只张翅欲飞的乌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