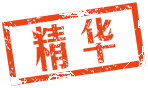|
|
进入秋季后,雨就一直下着,似乎未曾停过。
没有风雨故人来的惺惺惜之,亦没有听雨客舟中的惆怅隽永,唯有这一行被雨水打湿的文字,雾气腾腾,弥漫在字里行间我看不到的角落。一阵冷风吹散了第一段的第一行字,一股骤雨又淋透了第二段的第二行字,使整篇文章都湿漉漉的,懵然一停笔,便看见一行文字在雨水中闪着晶莹的光,然后,逐渐远去。
最喜儿时雨季。彼时,学校离家大约有四五里地之遥,每逢大雨时节,便会因乡村小道泥泞不堪而告假。和伙伴玩帅,捏泥人,引道路上一股股水流汇聚成溪,或于雨中而立,颇有大禹之气势。但终于还是不喜多于喜欢。雨时,最不喜出门,出去进来之间,会给家里带来满地泥污,免不了又要忍受批评甚或责骂。况且,逢见大雨,家里或者又会漏水,便拿着盆盆罐罐到处接雨水,儿时的我,大约是不喜体力活的。
雨微小时,上学之路便成了漫漫征程,大约世间再无比此更为遥远的路程罢,穿着雨靴,一脚浅一脚深的赶路,匆匆的吃完午饭,便又得匆匆的往学校赶。那个时候,便会特别羡慕路近些的同学,间或也会在要好的近些的伙伴家混顿午饭,便是这个时节最大的享受。
当然更多的是求学路上的乐趣。隐约记得当时还是很刻苦的,从来都是天不亮就要起床,风雪无阻,再冷的天,再深爱暖和的被窝,闹铃响起时,还会一激灵的从床上爬起,村前村后会叫起一群伙伴,然后结伴,浩浩荡荡,你追我赶,有说有笑,间或会用木棍点起火把,照亮漆黑的黎明,也照亮漫漫的求学路。
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也会因为有伙伴的陪伴而不显孤独,几个同龄的孩子通常会商量出十余种不同的回家的线路,或翻沟渠,或走土崖,或走村窜巷。还记得冬天时,翻沟渠,搬起一块巨大的石头,结果看见盘缠在石头下冬眠的蛇,还有落荒而逃的胆战心惊,或者走走土崖,有野枣树,勾起一堆枣子,和伙伴们你一颗我一颗的分食,为一颗红枣或一颗大枣而不亦乐乎。一幕一幕,总会有瞬时的温暖。还记得家门前那条小河,一年四季总有潺潺流水,有河草,有小鱼,甚至还有难得一见的螃蟹和泥鳅,夏天时,挽起裤管,顺河而上,便是一天难得的欢愉。小河的拐弯处,一棵白杨树苍老着,却还在倔强的生长着。我不知道这棵白杨树有多少年轮,或者爷爷的儿时,也是在这棵白杨树下欢愉的。以至后来,这棵树便成了这个村庄的代名词,方圆数里,你给任何乡亲打听白杨树在哪,都会有人给你遥指,再走走,不远就到了。
这样的路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从未间断,每日往返两次,直到五年级转校,方就此作罢。
没想到的却是,所有关于儿时的记忆,似乎都停留在了这漫长的四五里路程之上。后来,求学、工作,为生活打拼,回家的次数依稀可数,这条在儿时走过无数次的路,很少再走了。
时光如梭。童年仿佛是一场暴风雨,结束之后除了阳光什么都留不下。
城市一节节的拔高,乡村也在一段段的扩张,路上再偶遇一些孩提的伙伴,也只是依稀的有着似曾相识的面孔,却再也叫不上名字。这个乡村,也像这个乡村的这些面孔一样,逐渐模糊。
城市化依然以其巨大的能量,摧毁着我童年的故乡,并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着乡村中的每一个人。
白杨树的周边,因工业园的建设而显得蓬勃起来,人多了,车也多了。遍布着的工厂,让很多留守的乡村妇女们在洗衣做饭之余也能享受工业化的福利——起码,不用再背井离乡的出门打工了。同时,很多乡亲们也将新房盖在了白杨树的周边,那条下雨天总是泥泞的小路也铺上了柏油,出门不用穿雨靴了。而我却似乎发现,白杨树落寞了。
白杨树应愈加的苍老了罢,一多半的树杆都已枯萎、破损,露出一个巨大的树洞,被嬉戏的小孩塞进去了很多垃圾,树冠之上,叶子稀稀拉拉的繁衍着,这似乎是这棵树还顽强活着的唯一凭证。没有几个人去注意这棵树,我也只是在偶尔经过时默默的行一注目礼而已。我想,可能很多人也是和我一样吧。
那条小河,那条承载了我诸多记忆的小河也已经干涸,没有小鱼,没有泥鳅,没有儿时玩伴,连那些曾经还飘荡着的欢声笑语也消失无迹。河床还在,只是上边铺满了枯黄了的、从来没有人打扫过的落叶。我知道,即使没有水了,河床也不会被填平,它就像一条现代化的疤痕,泾渭分明,割裂着一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
再走这条从家通往学校的路时,忽然觉得它变得这么的短了,没几步就已走完。我的母校已破败不堪,和旁边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建筑相映成辉,我再不忍瞩目。
城市化来了,我和我的乡亲们避无可避。
再去那片被称为是西坡的麦地时,也被从未见过的景象所震撼。那是一个夜晚,族里的一位长辈去世了,作为晚辈的我,必须得在这漆黑的夜里,陪着叔父们去接祖宗们的灵位回家。在这夜里,当一行人小心翼翼的走上西坡之时,我的眼前豁然出现了一条灯火长龙,原来是高速公路要从这里经过,工人们正在紧张的连夜施工中。
我有些不知说什么才好,小时候的西坡是村庄的粮仓,大片的田地旺盛的成长着,父辈们在这里收获汗水,收获辛劳,收获粮食,收获来年的希望。孩提的我和伙伴们便提着水壶,端着午饭,给父辈们送到西坡上。田间地头里,大人们抽着烟,乐呵呵的笑着,我们便在其间嬉闹、玩耍,捉蛐蛐,撵蝴蝶。
旧时的西坡在我的记忆中是个遥远的地方,遥远到每次听见西坡这个名字,都会觉得要比上学的路程还要辛苦,当然,这里还埋葬着我的祖先,我爷爷的爷爷,不知道多少辈的祖宗都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然后在去世之后被埋到西坡的尽头,去守护着这片粮仓。
可是西坡终究变了,开始喧闹了。开始要接受城市化的洗礼了。
就着夜色,就着手电筒微弱的灯光,我走近了这片灯火长龙,各种机器嘶哑的声音将夜色撕裂,工地上有几条看门的狗远远的看见人来,便不停的撕咬着。我从工地下的涵洞穿过,刚下过雨的乡间小路泥泞不堪,我很艰难地躲避着涵洞下聚集的水。
待到墓地,一群人跪倒,行三叩首礼,烧纸,鼓乐手便就吹打起来,礼毕,男人们三三两两的聚到一起抽烟。我也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点燃了一根烟,我看着身后的工地,再看看身前的墓地,我很想和我这些从未谋面的亲人们说些什么,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若干年后,我也将被葬于此处。我想。
我的父老乡亲们都已逐渐苍老。
爷爷奶奶的电话里,总是叮嘱有时间多回家看看。而我却很惭愧,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我应接不暇,偶尔回家,也是来去匆匆。但是我能知道,爷爷奶奶们的眼睛里,隐藏了多少的渴望。孩提的伙伴们都已长大。即使偶尔相遇,也再也没有了昔日要把酒言欢、一醉方休的激情和冲动,是什么,让我们面色苍白,表情木讷?
时常坐在家门口,看门前的两棵柿子树枝繁叶茂,每当深秋时,奶奶都会催促我赶忙把树上的柿子摘下来。这两棵树是我家翻修老房子之后栽下的,时光匆匆,十多年竟然也一晃而逝,柿子树也长大了。坐在柿子树下,对面不远处,是一条从田地里破膛而过的公路,记得以前刚通路的时候有说真不适合看着汽车这样从眼前开过,我的眼前,本该是一片麦地或者玉米地或者油菜花地,甚或者应该是一片豌豆地或西瓜地或红薯地。却最不应该是一条公路,每天发出轰隆的杂音,打扰这个村庄的宁静。
是的,世界在变,世界一直在变,家乡于我那种根深蒂固的感情却从未随着这世界的改变而掺有丝毫杂质。我想,我终究是要在这里终老的,虽然,儿时的雨季已经再也不会让今天的我脚下的路泥泞不堪。
 该贴已经同步到 黑娃的微博 该贴已经同步到 黑娃的微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