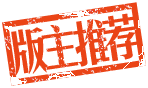老家康定有好多海子,可伴着我们成长的只有那眼小小的,像一滴泪珠似的海子。我一出生,就听大人叫它海子,除了海子好像没有其它名字。可有一天,我都长成粗壮的大男人了,才知道它真名叫放生池。啊啊,第一次听着真不习惯呢! 最不习惯的是,童年的海子遥远了,远得只能在梦里想想,永远也无法到达了。 我第一次去放生池,竟然不是去放生,而是去伤生。 那是小学时的一个暑假吧,我们几个小伙伴迷上了钓鱼。康定两条河,水都来自冰冷的雪山,还像山顶直冲而下的瀑布似的湍急,水里不适合鱼类生长,我信在河边坐上半天,才上钩一两条瘦棱棱的石巴子。好像是晋说的吧,头道桥菜园子那个海子里鱼多得很。我们心里便滑溜溜地滚出了那个海子,滚落到乱石嶙峋的郭达山下雅拉河岸,远远地看着一滴蓝,真像一滴冰冷的泪水。 我们都去那眼泪水里钓鱼。太阳很大,风也很大,风把太阳的热刮走了,只剩下烤人的干燥。坐在海子边上,水让风扇起圈圈细纹,根本看不清海子里的鱼。晋说,水清亮得像玻璃,可以看着鱼吃饵吃进了肚皮再拉钩。这让网一样的水纹罩着的海子,看不见鱼的影子,连扔进水里的浮漂子都看不见。可大狗的手还是沉了,大叫有东西在咬钩了。我们都感觉手心的沉重,线在水里扯得笔直,跳动着打得水面波波响。大狗首先把一条黑背大鱼扔向岸,鱼在地上跳,他快乐得裤子都跳掉了。我们都拉上了一条条鱼。在第二钩扔进水里时,附近菜园子村里的狗狂吠起来,接着一群穿黑穿灰的人拿着棍棒围了过来。 晋说坏了,这海子里的鱼是他们喂养的吧,我们成了偷鱼贼了。 我们慌忙扔下鱼竿,鱼也没拿就朝旁边荒草里逃。那里很多乱石,又是沼泽一样的水湿,有人跳起来,原来踩到蛇窝了,一条条大大小小的麻花蛇钻出来,又朝深深的草笼里钻去。我们终于逃掉了,跑过二道桥那座石桥,心还波波地跳,像我们钓起来的那些鱼。 也许是我们来闹了这一次,海子边上有人搭了棚,养了条牛一般大的藏狗,老远嗅到生人的气味就仰着脖子吠,声音像重槌擂鼓。 我们只有眼馋地远远望着那眼海子,眼睛望到酸痛时,真的滴下了串串泪珠子。眨眨眼睛再看海子,蓝艳艳的清亮亮的,不就是滴到山崖脚下伤心的泪珠子么! 那时去二道桥浴池没有公交车,我们爱一边玩着一边步行去泡五分钱的大澡堂。路过海子时,都爱停下来,酸酸地望着对岸山脚下那一汪蓝蓝的水呼叫,引得那条守湖藏狗愤怒狂吠。更多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坐在路旁望着那眼蓝色沉思,谁也不说话,但我们清楚,心里都有一条鱼在蹦跳。有时,我会冒出一句莫名奇妙的话:“你们发现没有,这里看海子像极了猫的眼睛。”我这样说,是我发现那眼湖水随天气阴晴,颜色会变化。晴天就蓝得耀眼,阴天又一团死黑,冬天时又一片灰白。大家望着海水,又忍不住笑,说我胡思乱想,假如是眼睛,它怎么不眨动呢?眼睛都会眨动的。我笑了,没告诉他们,那是注满了泪水的眼睛,假如眨动,苦涩的泪水一定会串串滚满,天呀地呀人呀都会伤心的。它怎么忍心眨动呢? 就在公路脚下,在那个破破烂烂的屠宰场旁边,也有一眼水池,同对岸的海子颜色一样,蓝色时蓝得耀眼,黑色时黑得伤心。在那里,我们听人讲过海子的传说,记得讲传说的是个穿中山装,上衣袋子里插着两支钢笔的男人,他站在那里给一群少男少女指着水池子讲,这池子里不能扔脏东西,就是因为弄脏了池子,一只雪白的天鹅才离开了这里,离开曾经开满花朵和果树的土地。他说,好久以前,对岸的那个海子是在这里的,那时海子很阔,水清亮如镜。海子四周绿树成荫,一年四季鲜花成片。后来,有人来了,把树砍了绿草平了,开成了菜地。菜农在海子里泡粪桶洗粪筐,旁边又开了个屠宰场,杀猪宰牛,呕臭的内脏就扔到海子里。
有一天,有个菜农正在海子里淘洗粪桶时,海子里呼啦啦飞起一只银白的天鹅,哀鸣声刺着他的耳鼓。天鹅伤心地越飞越高,在他头顶盘旋了好几圈,又俯冲下来,从他头顶擦过,好像在警告他什么。他看着天鹅,摇摇头又把粘满粪便的桶扔进海子里淘洗起来。呜哇,天鹅绝望地叫了一声,一滴血掉下来,在海水里一圈圈融化。朝阳变成了一片刺眼的银白,他眼睛都睁不开了,天鹅凄凉的鸣叫一直在他耳旁响着。声音越响越远,他看见海子水一点点消失了,旁边的草地树木也开始枯萎了。在水只剩一口时,他听见了天鹅远处的鸣叫,他真不相信自已的眼睛,在雅拉河的对岸,在那片乱石丛中冒出了一眼阔大的海子,水清明如镜,山崖怪石一下全倒映进海子里。天鹅漂浮在海子里,在海心里漂着漂着,就消失了。 听完他讲的故事,看着剩余的那一眼小小的池水,我们都皱起了鼻子,我们都嗅到了一股人粪的清香味。 春夏之交和初秋九月,海子四周的景色是最美的,也是最让孩子们快乐的。记得五月之初吧,山顶岩石上还染着霜雪,山脚海子岸的杨果树丛粉白粉白的花一串串开放了,像火焰燃烧一样的旺盛。杨果花就是杜鹃花,藏语叫达玛麦朵。我们用小砍刀砍一束束回来,插在酒瓶子里,满屋都是清香味。当然,最让我们开心的还是九月,那些小矮灌木丛里的野果子熟了,我们最喜欢采摘的是那种叫马鲜子的野果,成熟后的马鲜子红嫩嫩的,一片片生长着,有苹果的香味,又有葡萄一般的甜密多汁,吃多了还会饮了酒一样的沉醉。 采野果的时候,守湖人不会干涉,坐在门旁,把凶恶的狗关进屋内。他脸上晃动着湖水里反射的亮光,鼻尖上油亮亮的。好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模样,脸和手黑油油的,像收藏了多年的有油亮包浆的古董铜器。戴一顶帽沿下耷的呢帽,两鬓灰白,一只眼睛也是灰白的,看我们时,那只灰白的眼睛就细眯着,另一只眼睛张得老大,布满了红丝。记得,他叫我们把采的果子给他尝,还说有种跟马鲜子很像的果子不能采,那是毒蛇爬过的,会毒死人的。他细眯眼睛很狡猾地问我们,你们偷过海子里的鱼?我们脸红了,又失口否认。他哈地笑了,把一口鲜辣的兰花烟喷了我们一脸。他说,小杂种们,这海子里的鱼是弄不得的。这海子是菩萨的鱼池,鱼全是给菩萨喂养的。小杂种们,你们没看到吗?这海子心是通菩萨的莲花池的,好多鱼都是从菩萨的莲花池游过来的。 我们都不相信,又不敢把不相信告诉他。看着海子,靠岸的地方水清亮得像擦得干干净净的玻璃,水里的绿苔倒木石子都看得清楚楚。条条黑背鱼儿在水里悠闲地游着,像人吃饱了饭在散步。可海心却一团漆黑,时时有水泡子冒出来,真不知道那里有多深。胖子话多,说这水不是从河里浸过来的么?守湖人歪头看他,样子很凶,把兰花烟杆朝胖子肩膀上敲敲,烟灰洒了他一身。胖子跳开了,说难道不是么?守湖人说,你这杂种娃一看就是不爱读书不爱听老师讲课的,给你说了,这海子连通菩萨的莲花池,当然是从菩萨的莲花池子里流过的呀。你这耳朵,扇蚊子又太小了点。 我们都不相信这海子水是从菩萨莲花池流过来的,可又不清楚是从哪来的。 康定人好些人都在传说,湖里曾经捞起来个乌龟,背壳黑油油的像一块巨型鹅卵石那么大。龟壳上刻有铭文,很古老没人认得。有人把乌龟带到山对面雪山脚下的大海子放生,可几年后又在这个小海子里捞到了。难道这些海子真的是相通的吗?康定四处都有海子,像谁撒了一把珠子在这些雪峰巨石间,五色海、长海子、蛇海子、吊海子、大海子……难道它们都是相通的吧? 好些日子没去海子玩了,突有一天我们发现守湖人不见了,那条恶狠狠的狗也不见了。只剩下那座小木棚子歪歪斜斜立在风口上,门上锁着一把生锈的大铜锁。听附近菜园村的人说,守湖人死了,他亲戚结婚,喝醉了酒,半夜归家时,把湖水当作了阳光下的草地,一脚就踏了进去。第二天有人发现他时,人已泡得像猪皮一样灰白,那条狗守在湖边呜呜呜伤心地嚎着。 没了守湖人,这里又是我们的天下啦。不过,我们再不敢钓海子里的鱼,怕真是菩萨莲花池游来的生灵,钓了遭报应。眼馋地看着倒映山崖树林的海子,看着水里飘动的白云和云底下的水草游鱼,晋说了我们都想说的话,跳进海子里游泳。 脱光衣服,我有些担心了,说这海子很深吧。晋跳进水里,冷得哧哧啧着舌头,又哈哈笑着说,没事,在海子边上游,看看水还淹不过我的脖子呢! 我们都跳了进去,冷得牙齿都颤抖起来。太阳那么大,这水怎么这么冷呀,难道菩萨住在冰山呀。游着戏着,就习惯了那种刺进骨心的冷,就有在天空飞翔的感觉。漂浮在蓝天白云之上,山呀岩呀树呀全在自已身下。 晋说,他想游到对岸去。我看着就伸了伸舌头,说你能行吧,看看湖心深得不见底,会不会钻出个啥来咬你一口。他打了我一下,说别说不吉利的话。他抬头看对岸说,这算个啥,我大渡河那么急的水,都敢游到对岸去。他挥着手臂大把大把地朝对岸游去,在湖心身子顿了顿,我们的心都抓紧了,他甩了甩头湿漉漉的头发,身上朝上蹦了一下,手朝上抓了一下像在抓什么东西,落下来身子一歪就从湖心的深黑处绕了过去。他一把一把游得轻松了,到了对岸边朝我们得意地舞着手臂大喊大叫起来。 他又游了过来,对我们说,啥事都没有,只是游到湖心时,感觉身子突然变重了,身下的水没有了,像正从高空朝下坠落,落进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不过,你没害怕,害怕就完蛋了,你得像想你有翅膀会飞,身上使劲朝上蹦。我就那样,看看,啥事也没有还游了个来回。他得意极了,拖着我们像他一样去横渡海子。 我们跟着他,刚开始都没什么,越朝湖心游,心里越紧张,我们都感觉到有东西把身子朝水下拉扯。我害怕了,说不敢游了,要游回去。大狗也不敢了,跟着我朝回游去。晋满脸不高兴地骂我们是猪粪,没胆子还很臭。只有大胖和他一起游到了对岸。那以后,他就更看不起我们了。 他游海子游成了瘾,三天两头都去游,还逃课去游。他说游个来回后,感觉手臂上的肌肉都有骨头那么硬了。冬天很冷,海子边都结着冰,他说他还想跳下水去游游。我们都劝他,这冷的天,人会冻死在水里的。他哈地一笑,说我很想游到菩萨莲花池里去看看呢!他跳进水里,又冷得直咬牙齿,腮帮都冻紫了。我们都劝他上来,他看也不看我们,就扑进水里,挥手拍击着水,朝湖心那个深黑的洞游去。快到湖心时,我听见他喊叫了一声没劲了,好痛!就没声音了。人像个白点子在湖心旋着,冒了一串水泡子,他不见了。我们等了好久,湖心起雾了,深黑的湖压着湖面,又撕碎成灰蒙蒙的,像脏污的纱帐罩在湖面,我们啥也看不清了。 等了大半天,我们都慌乱得哭喊起来,附近菜园村的人来了,划着小船到了湖心,也啥也找不到了。村里人说,湖心真有无底的洞,过去就吞没过游湖的人,吞没了连骨头都不会吐出来。 那个夏日,高原小城从到晚都融在金灿灿的阳光里,肥厚的树叶草叶都透着油亮亮的光。这一天早晨,菜水井子街菜市场来了个苍老的喇嘛,袈裟破破烂烂,手腕和脖子后都生满硬壳似的污垢。有人叫,济公活佛来了,还跟着他唱“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甲甲多……” 他瘦削的脸恨着喊叫的人,嘴里低声咒骂着什么。他进了菜市场就直奔卖鲜活鱼虾的摊位。 他把买鱼的人全掀开,指着桶里的鱼对卖鱼人说,这些鱼我全买了。买鱼人疑惑地看着他歪着嘴笑,他火了,从怀里掏出的大袋子里装满了钞票,百元五十的都有。围观的人惊得直啧舌头,看不出呀,每天只看到他坐在寺庙前伸手要钱,想不到他暗藏这么多的钱。他对买鱼人说,鱼我全要了,多少钱你看着拿吧。那些买鱼人叫起来,怎么不给我们留一点呢,我们还等着鱼下锅呢!他火了,脸刷白,眼里能喷出火来,指着那些买鱼吃的人说,你们是想下地狱煎油锅吧?这些鱼我是买来放生的,懂不懂?吃放生鱼会下地狱的! 他单手提着装满鱼的桶,就朝市场外走去。我以为他会把鱼倒湍急的河水里,他没有,过了下桥就朝北门外走去。遇见认识的人打招呼时说,去放生池放生。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伴着我们成长的那眼清清亮亮的海子另有个名字:放生池。 我们跟着他走,第一次看到了在海子里放生。 老喇嘛先伸手进水,摸了摸水温吧,就捧着一条小鱼,对他说着什么话,我看见他眼睛一眯,有泪水滴了下来。他把鱼轻轻放进水里,鱼游动起来时,他还在水里搅动了一下让鱼游远点。他脱了靴子,把裤腿高高挽起来,提起桶就走进了海子,朝深处走去时站在岸边的我们都惊得叫起来。他回头,恨着我们,骂了句什么,就把桶全浸入了水里,鱼全部从桶里游出来,朝深水处游去,他呜啊呜啊喊叫起来,那一刻,我们都看见他泪满面。上岸后,他把早准备好的杉树叶堆成一堆,点上火,让浓香的烟子朝海面飘去。他低声念叨着我们都听不懂的经文,手挥动着,让桑烟飘得更开更远。 大狗问我,晋会不会偷吃这些放生的鱼。 我说,晋不会吃,晋也是鱼,一条放生的鱼。 此后,康定小城恢复的放生节,就是在藏历四月初一,佛主释迦诞生的那天吧。据说,放生池边很热闹,娜姆寺、安雀寺、金刚寺等好些寺院都会来做放生仪式,把好些大地的生灵放归自然,与天地同在。
|